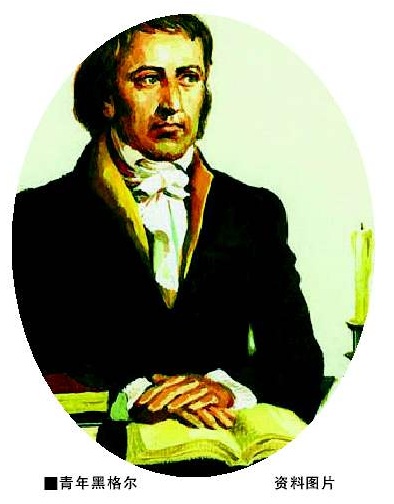
【核心提示】纵观中国文学史,因一句开风气式的口号而产生一个文学新时代的例子,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最典型的莫过于初唐陈子昂对“汉魏风骨”的呼唤,导致了“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新时期以来,这种变化已旁及文学研究领域且出现频率明显加速。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整个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重写文学史”所引发的系列变革等。时下,则有“宏大叙事”这一源自西方的术语,被用来对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与影响进行批评,从而颠覆性地改变了叙事文学观念与现状。
“宏大叙事”撼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使用“宏大叙事”一词,本是为了指明:那些具有现代性质的科学一直在利用历史哲学的元话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支撑元话语的就是宏大叙事,包括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与远大目标等。利奥塔的出发点,是质疑传统思辨哲学知识的合法性,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立场。其观点自20世纪末引入中国后,关于知识合法性的问题固然引起了学界重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宏大叙事”因对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的目标与弊病一语中的,立马“走红”,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宏大叙事主要指在历史哲学的引导下,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力求从纷繁芜杂的现象中提炼出历史发展的趋势、规律。这种文学观念,自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在中国文坛一直居统治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后现代思潮引进之后,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彼时对“文革”文学及“17年”文学的反思,已经走出“拨乱反正”阶段,开始从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等角度思考问题。后现代以差异性解构同一性的思路,正好提供了新视角:以前太注重同一性、普遍性,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对个体的忽略,当代文学曾有的弊病,可以归纳为偏重宏大叙事而忽略个体价值。
在无比庞杂的后现代理论中,“宏大叙事”不过是其中一个“气泡”,然而它竟能撼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现有格局,那一定是因为它的锋芒所指,既是后现代思潮的批判对象,又是已在中国学界扎下根来并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面貌的某种西学理论。首先致人联想的莫过于黑格尔的学说。
警惕“去黑格尔化”
消解对理想的执著
黑格尔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黑格尔学说的核心,就是追求普遍、展现“绝对理念”,在当下语境中,批评“宏大叙事”的理论内蕴,可以说主要就是“去黑格尔化”。
西方思想界的后浪推前浪是从不讲情面的,就在黑格尔学说达到顶峰之际,“去黑格尔化”已经开始了,且有不少还带着人身攻击的色彩。之外,在误解基础上“去黑格尔化”的声音颇为常见,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格鲁格先生的钢笔”。与黑格尔同时代的格鲁格,借批评谢林之名讽刺黑格尔:难道我手上的这支钢笔可以从绝对理念之类的纯粹概念里推演出来吗?
其实,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非抽象地谈论绝对理念,而是始终结合具体的自然、历史事实谈论问题,并认为历史是朝着既定方向发展的。他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的最高峰,自然界本身蕴涵着一个潜在的发展目标:一定会发展到出现人的阶段。因而,就目标而言,人先于自然,但在时间上实际发生的却是自然先于人。格鲁格误解了黑格尔,他在理解绝对理念的体现时,认为黑格尔主张自然界和人类是从纯粹概念里推演出来的。实际上,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体现,指的是它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展开、表达。也就是说,自然现象中一定包含着绝对理念,绝对理念一定体现在自然现象中,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黑格尔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强调人的意义在于使个人的东西变成普遍的东西,而国家就是“普遍”,因此个人的最大意义,就是属于国家,而不是停留在家庭成员的阶段上。所以他在谈论精神的伦理阶段时,特别强调家庭与国家是同一个伦理实体的不同形态。家庭属于伦理的“直接存在的形态”,国家则属于伦理的“自觉存在的形态”。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是摆脱了家庭、上升并参与国家生活的人生。
黑格尔学说本质上是为普鲁士国家说话的:他一直在论证个人服从国家的自然性和必然性。不少英国人和美国人,把黑格尔也当做法西斯的思想先驱,因为黑格尔关于战争、国家的理论确实如此:为了让人们放弃各自家庭的小利益,需要经常发动战争——战争能够使人舍家为国。
黑格尔学说的精要处,在于他从宇宙自然的运动中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提炼出来的绝对理念,与辩证法一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他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著名论断,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就是根据事物“正、反、合”的辩证运动规律来分析社会历史演进过程和特征的。所以,德勒兹这一后现代最激进的思想家,其“去黑格尔化”也最为彻底:连辩证法都要去掉。
黑格尔学说是“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的。问题出在“到历史中去”的时候,他往往为了追求完满而削足适履。比如,为了证明“正、反、合”三阶段的普遍性,将人的五官改为“三官”;为了证明德国统治世界的自然性、合理性,将欧洲说成是自然地理“正、反、合”发展过程的结果,即世界的中心,而德国又是欧洲的中心。世界中心的中心,不是世界领袖还能是什么?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去黑格尔化”声音中切中肯綮的越来越多。罗素的批评可谓独占鳌头:如果不相信“宇宙渐渐在学习黑格尔的哲学”,就得承认黑格尔的一些论点“需要对事实作一些歪曲,而且相当无知”。罗素以黑格尔为例,对哲学理论的价值判断所提出的建议尤其引人注目:不必追求完满,不完满的学说肯定不会全部正确,但完满的学说却可以错得离谱,只有那些自相矛盾的学说才会部分正确。
宏大叙事的存在,首先是继承传统使然。比如300多年前孔尚任就自述《桃花扇》的主题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彼时距黑格尔出生还有近100年。只是从当代文学的实际语境来看,宏大叙事的理论根源就绕不开黑格尔了:它来自“绝对理念”所衍生的同一性及其化身——历史哲学。通过对浩繁的宇宙历史资料的概括总结,黑格尔认定存在一个东西,于是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之、建构之、显现之。他对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无比坚定、无比执著而又无比成功。个人追求理想本是好事,但如果这理想被强权者当做普遍模式强力推广,结果是否如创始者所预期的那样可就难说了。
在当下语境中,借鉴后现代主张的差异性、私人叙事,不应停留在对同一性、宏大叙事的解构上,而是要像黑格尔那样,将自己认定的东西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如果“去黑格尔化”演变为完全消解、否定对理想的执著,那么,与将个人追求作为普遍理想强加给他人相比,结果也许会更令人震惊!当代文学与文论,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13002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130025号